
1934年,我父亲潘光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,我们全家随他迁居清华园。1935年,我姐姐潘乃穟到了入学年龄,进入成志小学一年级学习。据我母亲说,我那时不到入学年龄,也闹着非要去上学不可,于是,就把我送进了成志幼稚园。

清华附小筹备百年校庆的消息,唤起我无穷无尽的回忆。儿时的同学、伙伴他们都在哪里?在做什么?过得好不好?千丝万缕的记忆和牵挂重又回到我的心中:常振明、张益唐、陈国星、方志伟……,还有很多一生念念不忘的小学同学……

清华附小筹备百年校庆的消息,唤起我无穷无尽的回忆。儿时的同学、伙伴他们都在哪里?在做什么?过得好不好?千丝万缕的记忆和牵挂重又回到我的心中:常振明、张益唐、陈国星、方志伟……,还有很多一生念念不忘的小学同学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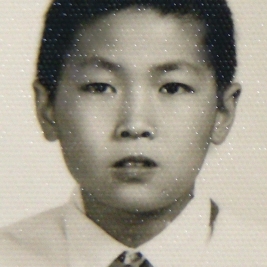
对我所在的1966届毕业生颠簸的人生里,我是幸运的,因为在小学短短的6年里,我遇见了两位好老师。刚上学时,我的班主任是田翠荣老师,乍看起来比我们大不了多少。四年级时,郭淑敏老师来到我们班,她说起话来总是面带笑容,办事更像男老师。

混沌懵懂之间,唱着“涛涛的乌苏里江,英雄的珍宝岛……”我们这帮刚满7岁的“小豆包”身背着各种各样的自制花书包屁颠屁颠地咧着嘴跨入了清华附小,那是1969年,班级是 “一连二排”。

7月4日上午,清华附小闻道厅传来阵阵歌声,这是为迎接百年校庆校友联欢活动而举行的校友合唱团启动仪式上,老中青各年龄层的60余名校友在毕可纫老师指挥下,高唱当年儿童歌曲。大家欢聚一堂,共忆童年美好时光,共叙师生之情,共谋为母校华诞演出献礼。

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有一天课还没有上完,好几个同学都趴在了课桌上,教室里靠两边墙坐着的同学齐刷刷地全都趴在桌子上。班主任毕可纫老师见状,断定是由于天气冷教室的门窗关闭过严,同学们中了煤气。她当机立断,打开门窗,将同学们一个个地往外送。


